服务热线
0717-6900007
0717-6900008
0717-6900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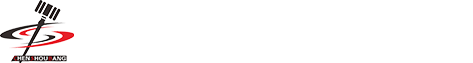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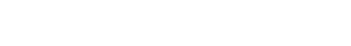
 湖北陈守邦律师事务所
湖北陈守邦律师事务所
劳动关系认定的基本思路 吴博文 一一摘自《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84辑
劳动关系的认定
(一)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质要件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劳动关系建立的要件是“用工”。此处的“用工”应作何理解?理论和实务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可以称为“实际使用说”。“实际使用说”认为,用工即劳动者的劳动力被用人单位实际使用或者消耗。该观点注重的是劳动力被实际使用的事实。另一种观点被称为“控制说”。“控制说”认为,用工即劳动者已将其劳动力使用权转让给用人单位,或者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力已取得使用权。该观点注重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处于被用人单位控制的状态,既包括劳动者的劳动力被实际使用,也包括劳动力虽然还未被实际使用但已经处于用人单位有权随时使用的状态。例如,劳动者虽未开始提供劳动,但已经被单位安排去熟悉工作环境、学习规章制度或者进行岗前培训等。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看,“控制说”对劳动者更为有利。实践中亦有地方立法采用“控制说”。比如,《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作为劳动关系建立时间的“用工之日”,是指劳动者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到用人单位报到之日。
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区别于普通民事合同中的用工,区别的关键在于其具有从属性,笔者认为,其从属性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用工的人格从属性。其侧重点在于,劳动者受用人单位控制程度较高,其从事何种劳动、运用何种手段劳动、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地点等事项,均受到用人单位较高程度的控制,能自主决定的程度比较低。比如,实践中存在的,自带车辆的司机与物流公司、运输公司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承揽之类的关系?判断这个问题,就可以看用工有没有人格从属性。如果司机每天接受单位的业务安排,在单位的指挥下开展业务,营运所得归单位,司机只是按照出车次数或者里程获得劳动报酬,那么双方之间就是劳动关系。如果司机并不接受公司的管理,而是有业务的时候就接受单位的安排,单位没有业务的时候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还可以承接其他单位的业务,此时双方之间就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承揽关系。
第二个层面,用工的组织从属性。劳动者的劳动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者因此就成为用人单位的劳动组织成员,在劳动中承担作为劳动组织成员所应负的遵守规章制度、保守商业秘密等义务。组织从属性可以弥补人格从属性的不足,将一些工作自主性较高、不宜纳入人格从属性范围的人员吸纳进来。比如律师对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对于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内部承包者对于企业。
(二)劳动关系认定的形式标志
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能查明是否存在用工的事实。这时候,就可以根据劳动关系的一些形式标志来进行判断和认定。所谓形式标志,是指由用工所映射出来的劳动关系的一些形式特征。比如书面的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还有像《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所提及的工资支付记录、工资发放花名册、社保缴纳记录、工作证、招聘登记表等。在劳动者不能直接证明用工事实的时候,如果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形式标志的存在,也可以帮助裁判者形成心证。当劳动者证明的形式标志足够多的时候,裁判者根据劳动者的举证,认为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用工的可能性高达一定程度时,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举证规则的规定,认定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认定劳动关系时,用工事实是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它决定着劳动关系的本质,也决定了形式标志,决定了何种现象和事实可以成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形式标志。但是,形式标志跟实质要件比起来,更具直观性,更容易举证,而且,一般情况下,形式标志与实质要件是统一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形式标志足够充分,就可以认定劳动关系。但是,当形式标志跟实质要件不一致的时候,还是要依据实质要件来认定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比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之前就已经订立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仍应以实际开始用工的时间为准,而不是以劳动合同订立的时间为准。
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合同等
普通民事合同时劳动关系的认定
建立劳动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换言之,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意思表示一致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劳动关系的建立,除了看用工之外,也要看民事主体双方有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因此,应当认为,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一句隐含了双方对建立劳动关系达成合意的推定。也就是说,对于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一句完整的解读应当是:囿于劳动者举证能力弱,只要其能证明存在用工的事实,法律就推定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并就此达成合意,而无需其就此举证证明。因此,反过来说,如果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的是建立其他法律关系的合意,比如单位提供反证证明双方订立了劳务、合作等民事合同,此时原则上应当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法律关系,否则有违意思自治原则,对单位来说也有失公平。但是,对于劳务合同、合作协议等证据,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实质性审查:一是审查合同内容,是不是名为普通民事合同,实为劳动合同;二是审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符合劳动关系项下的“用工”的本质特征,如果符合,仍然要认定双方存在的是劳动关系。
对劳务合同、合作合同、合作协议等作实质性审查的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防范用人单位利用自身优势支配地位迫使劳动者订立其他类型的合同,逃避劳动法上的义务。二是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要以民事主体之间实际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为准。三是从立法体系来看,相关立法并没有预设单位与个人形成劳务、雇佣关系的空间。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在劳动关系项下劳动者因工伤残或患职业病的,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原侵权责任法在规定用人者责任时,却只在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规定被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承继。可见,在法律层面,并没有规定个人受雇于单位,双方形成劳务、雇佣关系这种情形下,个人因提供劳务受伤害,该如何分担责任。但是鉴于我国民法典并未对个人与单位之间建立劳务、雇佣关系作出禁止性的规定,且实践中仍然存在这类似用工形式,当个人因提供劳务受伤害时,如果适用侵权法的过错原则来处理,则对个人很不利,会造成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因此,过往的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法院依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一条第一款来解决问题,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删除了上述条款。从上述分析可见,在法律的层面,单位与个人之间建立劳务、雇佣关系是不符合立法预期、不被立法鼓励的。综上,当我们审查发现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符合劳动关系中用工的本质属性时,即使双方订立的是劳务类合同,仍然要从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出发,遵循立法本意,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关系。